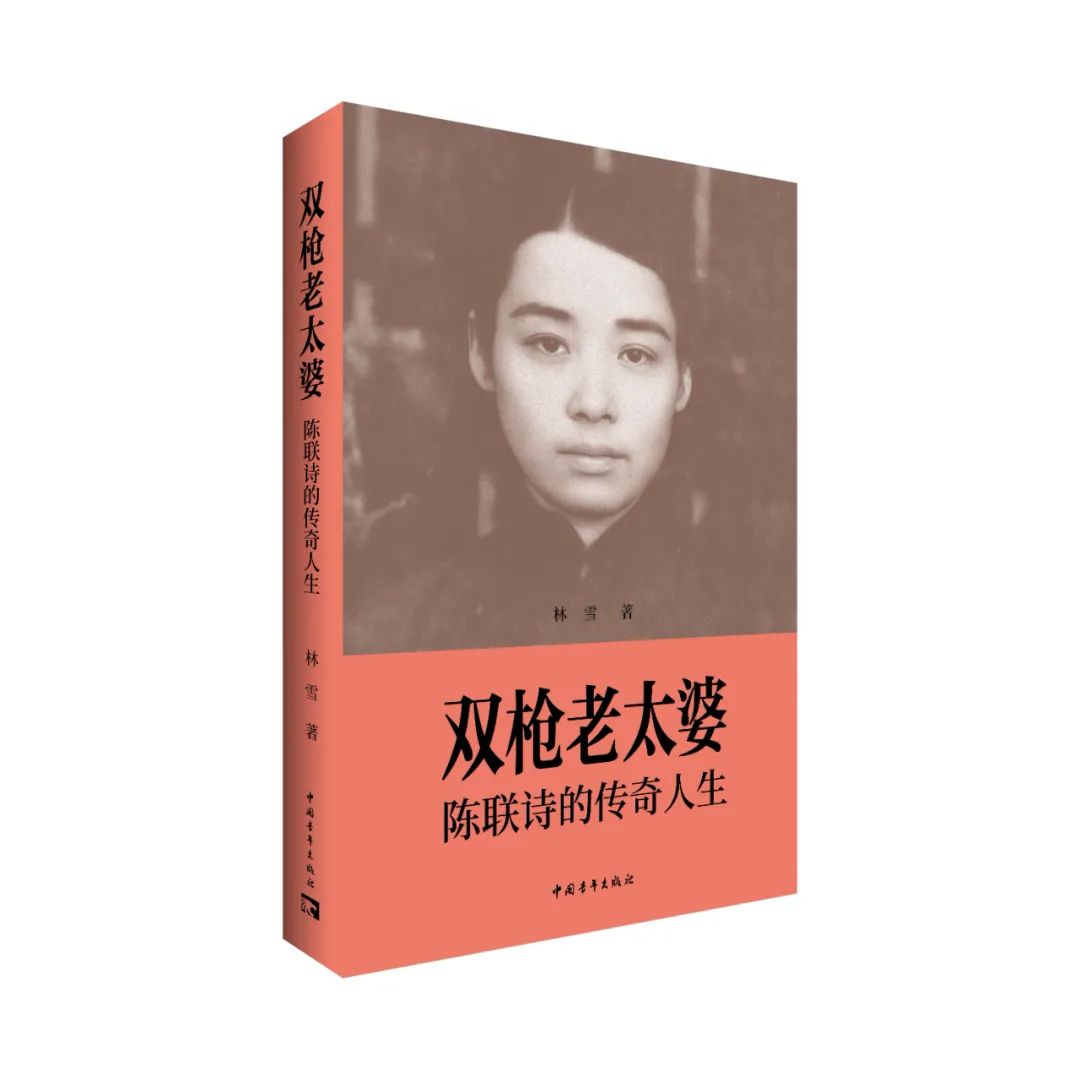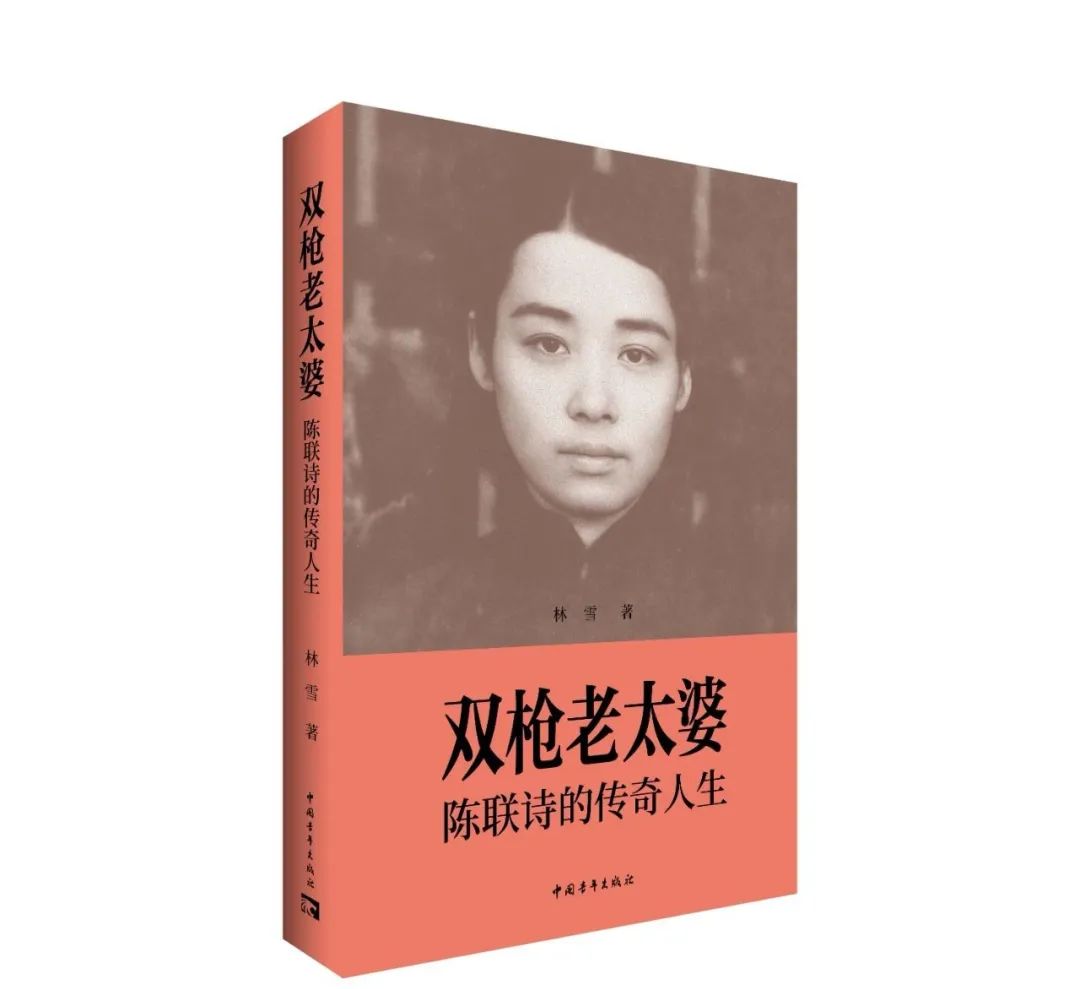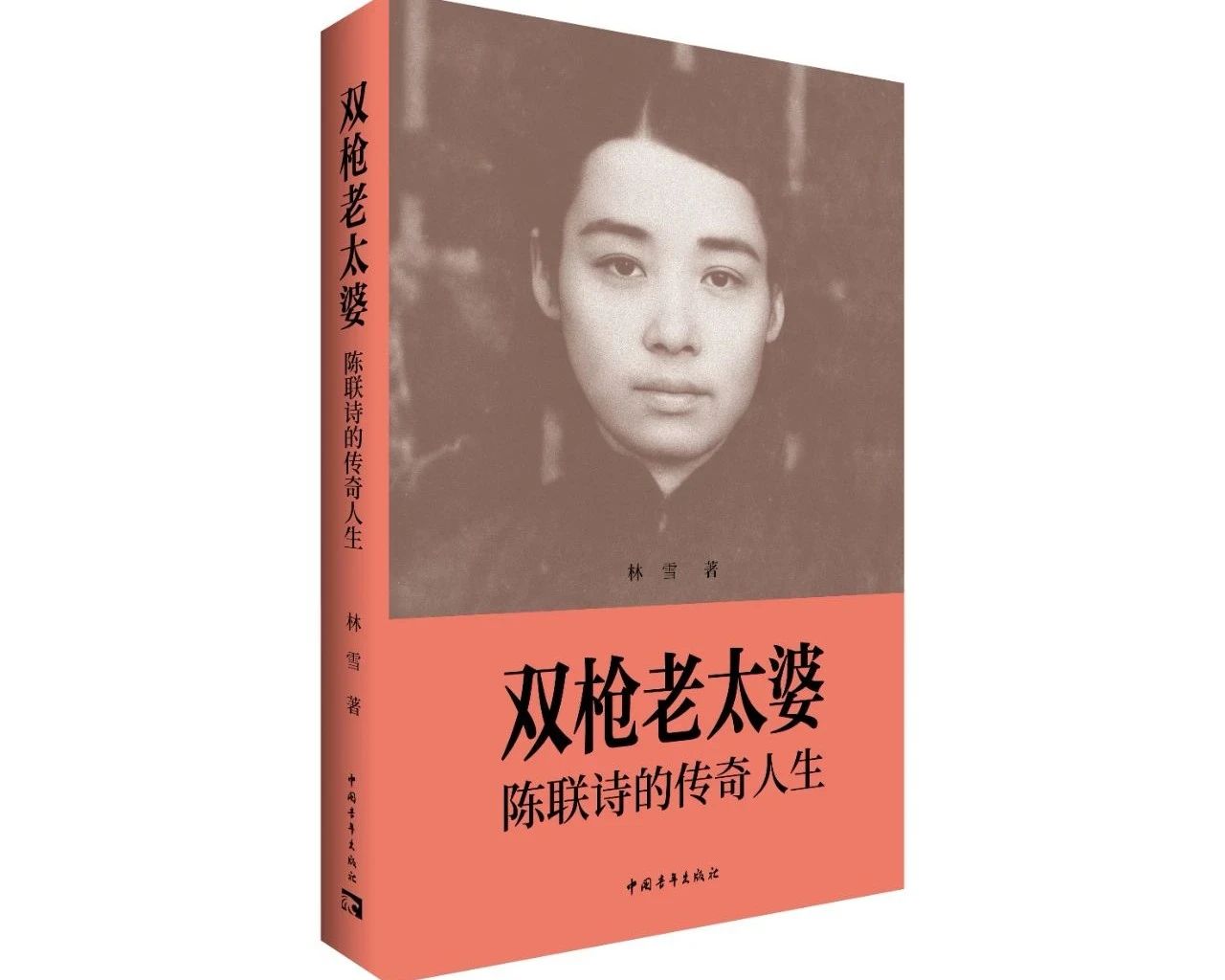1927年,陈联诗画的工笔画《姜太公稳坐钓鱼台》。
陈联诗是《红岩》中双枪老太婆的生活原型。
从大革命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她参与了川北华蓥山区三次武装起义,带着双枪在重庆与华蓥之间筹备枪弹等重要军需物资,指挥过多次重要战斗,丈夫廖玉璧牺牲后,她携一双儿女发誓“孤儿寡母闹革命”。在她和丈夫的影响下,家族中又走出了六位地下党员,为革命牺牲了四位亲人。
她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

第一代是我的外婆陈联诗,她留下来一部口述回忆录。这部回忆录记录了从她1900年出世至1949年的人生,是她生命中最为重要的经历。
陈联诗在华蓥山下长大,从大革命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她亲身参与了华蓥山区三次革命武装斗争,带着双枪在重庆与华蓥山之间闯荡。重庆刚刚解放,她的故事就流传开来,曾经写过《李勇大摆地雷阵》的著名作家邵子南到重庆担任西南文联副主席后,首先对陈联诗的故事进行记录,要为她“立传”。
1954年,邵子南帮忙将陈联诗调到了重庆市文联,这年的夏天连续三个晚上,就在重庆新民街三号文联的院子里为她举行了报告会,文联系统的四五十个创作人员都来听她讲华蓥山游击队的故事,其中就包括后来小说《红岩》的作者之一罗广斌。
1954年,陈联诗成为重庆文联美术家协会的专业画家。1959年国庆十周年之际,重庆市对外宣传画册上登载了陈联诗画竹簾的彩照。
邵子南因白血病去世前后,时任西南文联主席的老作家沙汀,就提出要将陈联诗的回忆录整理出来,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且专门组织了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两位同学帮她记录口述资料,还在重庆市对外宣传的画册上,登载了她作画的彩色照片,开始了对她的宣传。
几乎就与此同时,沙汀指导下的《红岩》创作也开始了,因为其中的主线——重庆地下斗争和渣滓洞、白公馆监狱斗争,与1948年华蓥山武装起义紧密相连;加上当时认为武装斗争才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主要因素,所以陈联诗的故事不仅能够表现她本人的传奇性,还能够提升这本主要反映城市地下斗争小说的“档次”,于是就当然成为书的一部分。
可是《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都是年轻人,其中的杨益言还是个学生。他们对于地下斗争和监狱斗争或许有些体验,可是对于农村的武装斗争就心中无数了。他们在陈联诗身上下了很多“功夫”来弥补这样的缺陷,不但对她进行了多次采访,还专门去华蓥地区陈联诗夫妇战斗过的地方熟悉生活。
甚至当《红岩》的责任编辑张羽欲将陈联诗的部分回忆录手稿寄回他所在的中国青年出版社,让三编室的主任江晓天看看能不能整理出版时,罗广斌还让他缓寄几天,把这些资料又仔细地看了一遍一可见罗广斌对于陈联诗故事的看重。
可是即使如此,他写作这一段时还是心中无数,又去向联诗大姐请教。陈联诗对罗广斌说:小罗,你就按照生活本身的样子来写。于是在《红岩》的前身《锢禁的世界》中,大段地采用了陈联诗的回忆录。
由于对两部作品的期望都很大,沙汀特地指示罗广斌说:“联诗大姐的故事另外要写一本书,你们书中关于她的情节不要用得太多了。”沙汀希望《红岩》中的“双枪老太婆”,是一个虽然着墨不多却很受读者喜欢的传奇人物——这一点果然不出他所料。
即使这样,后来写成的《红岩》中,还是保留了陈联诗的许多故事:比如晚辈林梅侠的丈夫陈作仪在渣滓洞大屠杀的突围中牺牲后,林梅侠成天像傻了似的,哭都哭不出来。陈联诗看了难受,就抱着她说:“梅侠,你就当着我们亲人的面哭出来吧,哭出来会好受一些。”在小说《红岩》中,这个情节就被写成了“双枪老太婆”和江姐见面的那场戏。陈联诗手上总是戴着一只玉镯,而且她在华蓥山区活动的时候常常坐着滑竿,于是《红岩》中的“双枪老太婆”出现在小茶馆时,就坐着滑竿戴着玉镯。
陈联诗还向罗广斌讲过:当年敌人把她关在岳池县的监狱里整整一年,也没有结果,就把她放出来,想“放长线钓大鱼”。谁知道当天晚上她就被山上派下来的二十多个同志秘密接走了,急得县长张俊昌冒着大雪追了她三十里路,后来张俊昌还因为这事情被撤了职。《红岩》中的“双枪老太婆”对警察局长说,“当年我越狱,你冒着大雪追了我三十里……”,这句台词显然是从这件事情演化而来。很多人都证实:电影《烈火中永生》中“双枪老太婆”的造型,是剧组在看过陈联诗的照片以后设计成的短发。
1960年的夏天,我的外婆陈联诗去世,四川省文联将刚刚摘去“右派”帽子的我的父亲林向北和我的母亲廖宁君借调到省文联,正式开始了对陈联诗遗稿的整理工作。
与对《红岩》的期望不同,沙汀希望我的父母把陈联诗的生平经历,不是写成罗广斌希望的“四川的《红旗谱》”,而是写成“中国的《战争与和平》”。记得当时还定下了一些写作方式上的设想,比如在体裁上为传记体小说;情节上以“串珠式”(而非“辫子式”)结构;等等。
父母先后十多次到家乡岳池县,访问了外婆陈联诗和外公廖玉壁的亲朋好友、邻里乡亲、当年的游击队员和农民、同情与支持过华蓥山游击队的民主进步人士、与之对立的保甲长和反面人物以及有关人士二百多人,收集了上百万字的资料和许多珍贵的文物,然后在沙汀、艾芜等大家的指导下,结合陈联诗的口述回忆录,陆续整理出一些篇章。
此时正值全国性大饥荒,也是我们家最困难的时期,父亲错划“右派”之后工资连降五级,不但要负担我们六个子女的生活、医疗和上学的费用,还有他和母亲四处奔走的费用。住房逼仄,父亲只得每天去茶馆写作,泡一碗5分钱的“三花”(即三级花茶末)喝一天,中午吃一个6分钱的锅盔(烧饼)。
这期间,陈联诗的回忆录也引起各家出版社的注意。大约是1961年的秋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社长、总编辑韦君宜到四川组稿,经四川省作协推荐看了刚刚整理出来的那些篇章,在四川宾馆约见了我的父母,10岁的我有幸随行。这次约见,韦君宜决定将这部书稿作为该社的重点项目来抓,并指派小说组组长王仰晨做这本书的责任编辑。
1962年5月14日,罗广斌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写过一封信,信中谈了十个问题,其中谈得最多的,就是关于陈联诗的这部回忆录:
陈联诗(《红岩》中的双枪老太婆的原型)的遗稿,现在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我曾多次各方面鼓吹,也曾向你们谈过),省文联已将陈的女儿廖宁君、女婿林向北二人调出来,专门整理写作,这是一件大好事。
最近,廖、林二人来渝收集资料,也找了我们,我们鼓吹他们认真写好,弄出一部四川的《红旗谱》。林廖均有文化,又是地下党的干部(林后来成为右派,现在脱了帽子),且情况熟悉,是有条件写好的。我只有一点担心:他们求成心切,对困难(指提高作品的思想、战斗力方面)估计略少,但是,很多领导同志的关心,还有沙汀同志在掌舵,问题是不大的,写好的可能性相当大。何况一稿不成可以二稿三稿,直到成功。
……现在人民出版社读了原稿(你们见过的),认为大有搞头,已派王仰晨来川,跟着林、廖在跑,看样子,人家人民出版壮准备花点本钱,意在必成。
……
不仅是出版社了。接下来还由文化部主管电影的副部长夏衍拍板决定:拍完由《红岩》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就拍陈联诗。只是后来因为“文化大革命”很快爆发,夏衍本人和《烈火中永生》都受到批判,此事搁浅。
1964年,我的父母在生活环境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终于完成了四十万字的初稿《华蓥风暴》,在四川省文联为这部油印稿组织的讨论会上,许多行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积极的支持,罗广斌做了专题发言,认为这部书稿不但可以在国内出版,而且可以走向世界。
正当各方积极准备将《华蓥风暴》修改出版的时候,“四清”开始了,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一切都变了调。一个当初参与记录陈联诗口述回忆录的人甚至对此书“反戈一击”,令很多人都受到了牵连,沙汀自然是首当其冲,我们全家也因为这本书被“打入另册”。
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父母却受到了茅盾先生的关怀。先生先是受我父母之托,找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韦君宜同志了解书稿的情况,接着又在没有办理退稿手续的情况下,取回了那套完整的《华蓥风暴》并寄到我家。此时我家因为多次被抄,资料散失严重,得到这套书稿真是如获至宝。
1975年,我的母亲廖宁君因为忧愤成疾,不幸去世,茅盾先生知道后,立即寄了三十元钱,托人送来花圈,并写来一封非常诚挚的信,信中说:“革命前辈联诗同志玉照英姿飒爽,觉小说《红岩》描写之形象赫然在目,钦仰无限,事业永在,将来历史自有评论,《华蓥风暴》目前未能问世,幸原稿尚完整,正如沙汀艾芜两同志所说,当俟诸他日。所有尊惠照片当珍藏,亦以你家革命家史自勉,且勉励儿孙辈也……”
打倒“四人帮”之后,沙汀曾经多次催促父亲完成此书。1992年7月12日,父亲与胡蜀兴(罗广斌同志的遗孀)和我还有我哥林民涛等人去看望沙汀前辈的时候,他已经双目失明,听说父亲决定带领我们重新整理这部书稿,他很高兴地说:“早就应该这样了。快点搞出来,出版了送一本给我,我让他们念给我听。”
接着父亲又带着我们去省医院干部病房看望大作家艾芜,艾芜很感慨地说:“这件事情只有你们自己才能够做好。这些年有人利用陈联诗的故事,胡编乱造了一些东西,弄得不伦不类的,陈联诗如果地下有知,一定会生气的。”基于这样的感慨,他为还没有出版的这本书题词:“把真实的联诗同志介绍给读者。”
此时我在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做记者编辑,工作之余不仅重读了《华蓥风暴》,还重读了外婆的口述回忆录原始记录本,并参考了大量的党史、文史资料;年逾古稀的父亲日夜兼程,赶写出十多万字的资料,补充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我哥林民涛忙里忙外,承担了大量的辅助工作。
两年以后,我终于完成了五十多万字的初稿,1994年借着上京采访的机会,将书稿带到北京,找到了母亲在“孩子剧团”的团友、老作家陈模,由他将书稿推荐到中国青年出版社。
中青社时任总编辑陈浩增和副总编辑郑一奇对于书稿非常重视,他们与陈模一起,从全书的立意、人物塑造、情节筛选等方面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并要求尽快出版。
由于我工作繁忙,社里还与中宣部文艺处联系,通过四川省委宣传部向我的工作单位打招呼,给我请了六个月的创作假。六个月之后,我带着修改过的书稿再去北京,住在中青社的地下室里继续改稿;5月,我找到正在脑梗恢复中的韦君宜老人,她欣然为书稿写了序言,详述了当年她与此书的前因后果;接下来我将丈夫叫来北京,一起参与校对……1995年8月,50万字的《“双枪老太婆”:陈联诗自述》终于出版。
《“双枪老太婆”:陈联诗自述》并没有按照沙汀当初设定的“传记体小说”而是以非虚构的写作方式,披露了陈联诗的真实命运,打动了众多读者,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时就有57家传媒予以报道,数家报刊予以连载。在继后的28年里,媒体对于这个题材紧追不舍,出了四部纪录片,还有大量各种形式的专题采访和文章。一时间屏幕上到处都是手挥“双枪”的女人,恐怕也与此书有些关系。
光阴荏苒,28年又过去了。去年我的父亲以106岁的高龄辞世,我也从中年走到了老年,与中青社重续旧缘,接受了此书的再版工作。想当年,我还是一个奔跑在一线的新闻记者,整理陈联诗的回忆录,不过是扒梳资料,厘清脉络,寻找旁证,繁衍成篇,一心一意只是为了完成外婆的遗嘱、家族的托付,在文字上是很粗疏的。
尽管陈联诗一生的经历都很精彩,这次再版,我只是截取了她从少女时代到整个游击队解体、自己只身远赴苏联这一段。这是她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段,故事情节紧凑,人物形象鲜活,命运又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很容易引人入胜。
可是当那些补充史料、删繁就简之类的技术活完成之后,我却再也改不动了,原因很久找不到,最后恍然大悟:因为这些都是陈联诗亲身的经历,又是她亲口叙述,很多地方都保持了她的原话和当时的社会面貌。这些元素不是来自二十多年前我整理的那部书稿,而是来自一百多年前的社会现实。它们以自己真实的面貌,骄傲地挺立在那里,纹丝不动。
这些撼不动的文字,叙述了一支革命队伍在那个年代从诞生到沉寂的过程,以及女主角在这个过程中的成长。它首先能够满足人们最感兴趣的话题:陈联诗是怎么样从一个书香门第的闺阁女子,成长为那个赫赫有名的双枪女人的。但是更有意义的,是这本书会纠正人们对于革命的一些误解,特别是对于革命中人的误解。
比如,革命是暴力,但不仅仅是一个阶级推翻另外一个阶级的暴力,而是所有的人联合起来推翻压迫在自己身上的恶势力,所以革命的队伍既浩浩荡荡也形形色色。革命也不全是打打杀杀,其中还有进退,有分合,有人情世故,有利益纠葛,当然也会有权谋。这本书还让我们看到了百年前那个新旧交替的社会环境里,有一种人可以突破所有的界限,受到所有人的尊敬,比如陈联诗。
三代人写成的一本书,穿过百年历史风雨一路走到了今天,限于功底浅薄,我到底没有能够把它写成老作家沙汀所希望的“中国的《战争与和平》”,不过我已经尽力了。
值此书再版之际,谨代表我的全家,更代表九泉之下的前辈,向从最初开始所有关怀和帮助它的人们,一一鞠躬致谢。更要感谢中国青年出版社,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初次接触,到九十年代的初版,再到今天的再版,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几代领导和编辑都为这个题材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天意玉成,众人抱薪,书中那些牺牲了的人们在天堂俯视,应该是多么的欣慰。
本书主人公陈联诗是《红岩》中双枪老太婆的生活原型。从大革命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她参与了川北华蓥山区三次武装起义,带着双枪在重庆与华蓥之间筹备枪弹等重要军需物资,指挥过多次重要战斗,丈夫廖玉璧牺牲后,她携一双儿女发誓“孤儿寡母闹革命”。在她和丈夫的影响下,家族中又走出了六位地下党员,为革命牺牲了四位亲人,她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
书中以陈联诗从少女时期到丈夫牺牲后只身远赴苏联的曲折过往为主线,再现了一位出生书香门第的大小姐、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教员为了国家命运走上革命道路、成为双枪老太婆的传奇经历。
林雪,陈联诗外孙女,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当过知青、工人、广播记者、报纸编辑。1981 年开始写作,代表作品有《“双枪老太婆”:陈联诗自述》《留学大调查》《亲历者》等专著。
双枪老太婆:陈联诗的传奇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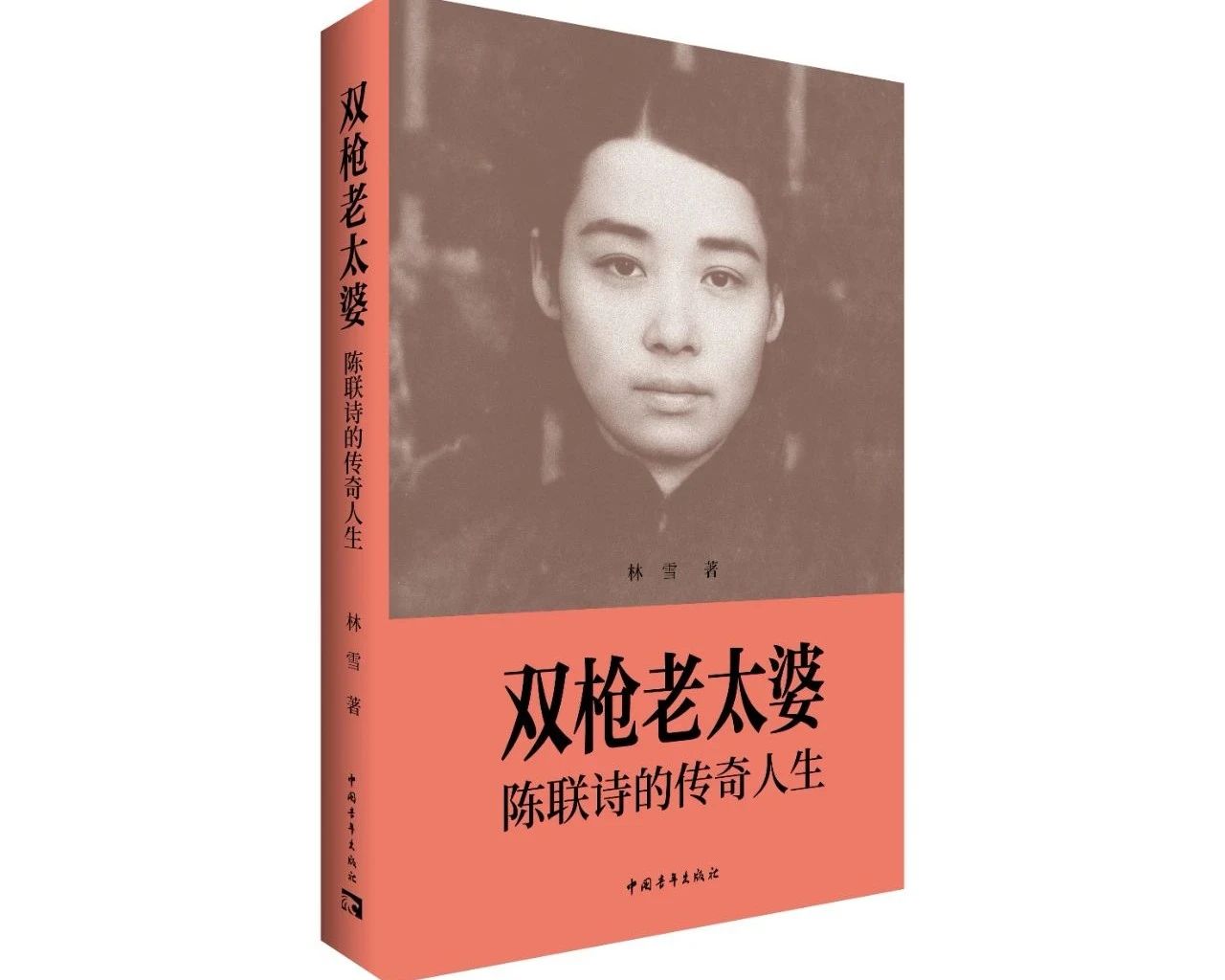
小程序